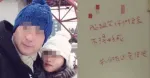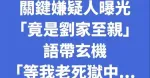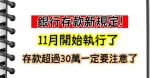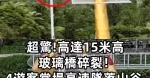1/4
下一頁
漢文帝高級捧殺,讓弟弟劉長70人40輛車就敢造反

1/4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劉恆不是親手殺了弟弟劉長,卻又的確把人一步步逼進死路。這不是刀槍血戰,而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權力「捧殺」。70人、40輛車,一場看似光鮮的流放旅程,結果是王爺絕食自盡。這才是真正的「殺人不見血」。
皇帝捧弟,捧出個「造反王」
起初,劉恆和劉長的兄弟情還算體面。一個是母憑子貴的代王,另一個是呂后的外孫,雖非一母所生,卻在皇權洗牌中各自翻了身。漢高祖劉邦去世後,朝局風雲變幻,呂氏一脈興盛又驟亡,劉恆靠著沉穩、低調的風格拿下皇位。即位後,他成了歷史上有名的仁政皇帝——漢文帝。
面對親弟弟,他也沒少下功夫安撫。封王、賜地、賜車馬,還時常賞賜美女金帛,連朝中大臣都看不過眼。劉長被封為淮南王,坐鎮南方富庶之地,擁有龐大封地和強力兵權。一個邊郡王,過得比宮中太子都滋潤。
淮南王不是個省油的燈。吃好喝好後,就想多點事做。他開始擴充私軍,任用親信,建宮造苑,朝廷派去的監察官基本被架空。誰勸他收斂,誰就被調走或者貶謫。他看朝廷沒動作,自信心飆升。自詡才智不遜兄長,自問皇位本也該輪到自己。
漢文帝聽說了,但不動聲色。他繼續賞賜,不但沒削權,反而再添人手,陸續調撥物資。有人懷疑他太軟,臣子袁盎私下提議乾脆廢了淮南王,被文帝輕描淡寫地駁回。看上去像是寬厚,其實是給劉長套上一層更緊的軟網。
宮廷中的風向也變了。朝臣們越來越不待見淮南王,嘴上不說,心裡都明白:這人越得寵,就越危險。朝廷制度本來就有諸侯制衡的結構,一個人權勢過大,帝王反倒要收回手中的籌碼。
淮南王根本沒意識到這些。他覺得哥哥是老好人,皇恩浩蕩,信他愛他,不會動他。於是他就更放肆,甚至開始和匈奴、閩越暗通款曲。資料明確記載,他秘密派人前往邊境,與外族使節私下交涉,還讓人探聽朝中動向。
一個王爺私通外族,按律當斬。但漢文帝沒有下令誅殺,只是宣布廢王,將劉長降為庶人,流放至蜀郡嚴道。這一紙詔書,看似寬宥,實則重擊。劉長從高高在上的封王,驟然跌入塵埃。這種心理落差,比砍頭還難受。
這時才出現70人護送、40輛車的場面。名義上體面流放,實則把人一步步趕進死角。面子有了,命卻保不住。人被廢、權被削、名被剝,只剩下一身王爺的架子,卻要步行去戍邊苦地。這不是處決,是軟性圍殺。
那一年,劉長的命還在,但尊嚴全無。他沒能讀懂兄長的殺機,直到踏上流放路時才意識到,最狠的手段不是一劍封喉,而是一場假裝寬容的制度清算。
七十人送行,送的是條不歸路
車隊動身那天,劉長穿著王袍站在府門前,目光渙散。朝廷派來押送的護衛不多不少,七十人,正好能護一位貴人走遍川蜀。而跟隨的馬車卻有四十輛,裝滿了御賜食物、舊日衣物,連妾室也帶了幾個。這陣仗不小,擺明了是給天下人看的——皇帝沒動刀,是弟弟自己犯事自取其辱。
從長安出發,路過雍縣、扶風、巴郡,一路向南。蜀郡地勢偏僻,氣候濕熱,是文人墨客都不願居之地。一個從小在都城長大、習慣奢華的王爺,要在那裡度過餘生,堪比流放北疆。對劉長來說,這不只是貶謫,更是放逐。
車隊到達雍縣時,已是七月酷暑。人困馬乏,氣氛壓抑。這時劉長突然下令不進膳、不飲水。有人勸阻,未果。第三天,他開始發燒。第五天,體溫驟降,四肢抽搐。第七天,停止呼吸。
沒有人敢大聲說這是絕食抗命,更沒人敢說皇帝故意逼死親弟。史書只寫一句「至雍,卒」,寥寥數字,遮掩了一個王爺生前的所有掙扎。
漢文帝接到死訊後,據說「涕泣」,下令以王禮厚葬,還特地撥出三十戶人家守陵。表面做得光鮮,但誰都知道,這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清算。不給你下死手,卻讓你走投無路,這是帝王術的高級操作。
劉長死後,淮南國也隨之消失。漢文帝趁機將其子分封三處,拆散勢力,徹底抹除隱患。這套操作從頭到尾都沒有血光,卻殺得利落、乾淨,連百姓都看不出破綻。
殺人不見血,不一定是陰謀,更不一定需要刺客。用賞賜吊起你的胃口,用寬容推你上高台,再用制度剝你衣冠,讓你在萬眾矚目中自行了斷。這種殺人方式,比任何一次政變都隱蔽,也更讓人寒心。
劉長這條命,看似是他自己不要的,實則是一步步被「捧」上絕路。他信了兄長的慈悲,卻沒看透權力的深井。漢文帝這招,不動刀兵,卻比刀兵更傷人。歷史記住了這個過程,稱之為「捧殺」。
帝王無情,制度比刀更鋒利
皇帝如果真的要你死,並不一定會派人拿刀,而是慢慢削你羽翼,讓你失去依靠、自斷後路。劉長這事,表面看是自食其果,背後卻藏著漢文帝深思熟慮的一盤大棋。讓你從王爺變階下囚,還得自己走完流程,不冤枉,不血腥。
死訊傳回長安時,朝中沒人議論。這不是忌諱,而是默認。一個王爺犯錯被廢,流放途中絕食身亡——聽上去太合理。文帝表面悲傷,下令按王禮厚葬,還特意劃出三十戶守陵,給弟弟保留「王侯之儀」。看起來體面,實則徹底結束這場兄弟間的權力過招。
劉恆不是親手殺了弟弟劉長,卻又的確把人一步步逼進死路。這不是刀槍血戰,而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權力「捧殺」。70人、40輛車,一場看似光鮮的流放旅程,結果是王爺絕食自盡。這才是真正的「殺人不見血」。
皇帝捧弟,捧出個「造反王」
起初,劉恆和劉長的兄弟情還算體面。一個是母憑子貴的代王,另一個是呂后的外孫,雖非一母所生,卻在皇權洗牌中各自翻了身。漢高祖劉邦去世後,朝局風雲變幻,呂氏一脈興盛又驟亡,劉恆靠著沉穩、低調的風格拿下皇位。即位後,他成了歷史上有名的仁政皇帝——漢文帝。
面對親弟弟,他也沒少下功夫安撫。封王、賜地、賜車馬,還時常賞賜美女金帛,連朝中大臣都看不過眼。劉長被封為淮南王,坐鎮南方富庶之地,擁有龐大封地和強力兵權。一個邊郡王,過得比宮中太子都滋潤。
淮南王不是個省油的燈。吃好喝好後,就想多點事做。他開始擴充私軍,任用親信,建宮造苑,朝廷派去的監察官基本被架空。誰勸他收斂,誰就被調走或者貶謫。他看朝廷沒動作,自信心飆升。自詡才智不遜兄長,自問皇位本也該輪到自己。
漢文帝聽說了,但不動聲色。他繼續賞賜,不但沒削權,反而再添人手,陸續調撥物資。有人懷疑他太軟,臣子袁盎私下提議乾脆廢了淮南王,被文帝輕描淡寫地駁回。看上去像是寬厚,其實是給劉長套上一層更緊的軟網。
宮廷中的風向也變了。朝臣們越來越不待見淮南王,嘴上不說,心裡都明白:這人越得寵,就越危險。朝廷制度本來就有諸侯制衡的結構,一個人權勢過大,帝王反倒要收回手中的籌碼。
淮南王根本沒意識到這些。他覺得哥哥是老好人,皇恩浩蕩,信他愛他,不會動他。於是他就更放肆,甚至開始和匈奴、閩越暗通款曲。資料明確記載,他秘密派人前往邊境,與外族使節私下交涉,還讓人探聽朝中動向。
一個王爺私通外族,按律當斬。但漢文帝沒有下令誅殺,只是宣布廢王,將劉長降為庶人,流放至蜀郡嚴道。這一紙詔書,看似寬宥,實則重擊。劉長從高高在上的封王,驟然跌入塵埃。這種心理落差,比砍頭還難受。
這時才出現70人護送、40輛車的場面。名義上體面流放,實則把人一步步趕進死角。面子有了,命卻保不住。人被廢、權被削、名被剝,只剩下一身王爺的架子,卻要步行去戍邊苦地。這不是處決,是軟性圍殺。
那一年,劉長的命還在,但尊嚴全無。他沒能讀懂兄長的殺機,直到踏上流放路時才意識到,最狠的手段不是一劍封喉,而是一場假裝寬容的制度清算。
七十人送行,送的是條不歸路
車隊動身那天,劉長穿著王袍站在府門前,目光渙散。朝廷派來押送的護衛不多不少,七十人,正好能護一位貴人走遍川蜀。而跟隨的馬車卻有四十輛,裝滿了御賜食物、舊日衣物,連妾室也帶了幾個。這陣仗不小,擺明了是給天下人看的——皇帝沒動刀,是弟弟自己犯事自取其辱。
從長安出發,路過雍縣、扶風、巴郡,一路向南。蜀郡地勢偏僻,氣候濕熱,是文人墨客都不願居之地。一個從小在都城長大、習慣奢華的王爺,要在那裡度過餘生,堪比流放北疆。對劉長來說,這不只是貶謫,更是放逐。
車隊到達雍縣時,已是七月酷暑。人困馬乏,氣氛壓抑。這時劉長突然下令不進膳、不飲水。有人勸阻,未果。第三天,他開始發燒。第五天,體溫驟降,四肢抽搐。第七天,停止呼吸。
沒有人敢大聲說這是絕食抗命,更沒人敢說皇帝故意逼死親弟。史書只寫一句「至雍,卒」,寥寥數字,遮掩了一個王爺生前的所有掙扎。
漢文帝接到死訊後,據說「涕泣」,下令以王禮厚葬,還特地撥出三十戶人家守陵。表面做得光鮮,但誰都知道,這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清算。不給你下死手,卻讓你走投無路,這是帝王術的高級操作。
劉長死後,淮南國也隨之消失。漢文帝趁機將其子分封三處,拆散勢力,徹底抹除隱患。這套操作從頭到尾都沒有血光,卻殺得利落、乾淨,連百姓都看不出破綻。
殺人不見血,不一定是陰謀,更不一定需要刺客。用賞賜吊起你的胃口,用寬容推你上高台,再用制度剝你衣冠,讓你在萬眾矚目中自行了斷。這種殺人方式,比任何一次政變都隱蔽,也更讓人寒心。
劉長這條命,看似是他自己不要的,實則是一步步被「捧」上絕路。他信了兄長的慈悲,卻沒看透權力的深井。漢文帝這招,不動刀兵,卻比刀兵更傷人。歷史記住了這個過程,稱之為「捧殺」。
帝王無情,制度比刀更鋒利
皇帝如果真的要你死,並不一定會派人拿刀,而是慢慢削你羽翼,讓你失去依靠、自斷後路。劉長這事,表面看是自食其果,背後卻藏著漢文帝深思熟慮的一盤大棋。讓你從王爺變階下囚,還得自己走完流程,不冤枉,不血腥。
死訊傳回長安時,朝中沒人議論。這不是忌諱,而是默認。一個王爺犯錯被廢,流放途中絕食身亡——聽上去太合理。文帝表面悲傷,下令按王禮厚葬,還特意劃出三十戶守陵,給弟弟保留「王侯之儀」。看起來體面,實則徹底結束這場兄弟間的權力過招。
 呂純弘 • 5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