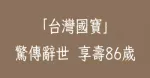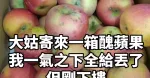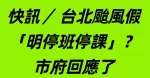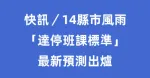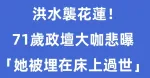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6歲女童給乾隆女兒做伴讀,卻被乾隆一眼看中,統領後宮54年

2/3
她不僅「母憑子貴」,被嘉慶提為貴妃,更因此一步步走入帝後的軌道。
自此,她不再只是那個曾為公主伴讀的小宮女,也不只是安於王府一隅的側福晉。
她開始參與內廷事務,打理中饋、掌管禮儀,連宮中都傳來了她賢良持家的名聲。
而她的父親恭阿拉,也因女兒之貴,被提拔為從三品官職,一家人總算過上安穩光景。
可這位鈕祜祿氏依舊不驕不躁。
鳳冠加身
乾隆六十年,當年的英武皇帝早已白髮蒼蒼,卻依舊精神矍鑠。
他雖早已決定退位,卻不願捨去「太上皇」的尊號與權力。
彼時的乾隆,雖讓皇子顒琰登基為帝,改元嘉慶,但宮中宮外誰都明白,這座帝國的真正舵手,依舊坐在那座養心殿里。
正是在這個微妙的交接時刻,鈕祜祿氏迎來了人生的又一次躍遷。
嘉慶元年正月初四,皇帝剛剛繼位第四日,便下旨冊封她為「貴妃」。
這道聖旨不是單純的禮數,而是朝廷對她多年來德行的肯定。
而讓這段榮寵更進一步的,是嘉慶二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喪禮。
皇后喜塔臘氏因久病無愈,不幸崩逝,享年不過三十餘,消息傳出,整個內廷哀悼不已。
皇后之位空懸,皇帝需要一位能穩定後宮、替他料理內務的中宮之主,諸妃中,惟鈕祜祿氏最為合適。
這一次,冊立未如往常那般倉促行禮,而是遵循太上皇定下的規制,需守先皇后喪期二十七月後,方可行冊立大典。
於是在嘉慶二年,她先被晉封為「皇貴妃」,暫攝六宮之政,直到嘉慶六年正式立為皇后,移居儲秀宮。
這期間,六宮之中風起雲湧。
皇貴妃位高權重,又年紀不大,朝中有人言她「受太上皇之恩,恩寵深厚」。
宮中也有舊妃暗中譏諷:「出身寒微,焉能掌後宮?」
她聽得多,卻從未回過一句,只以實際行動回應流言。
她每日親自督查各宮膳食衣物,遇嬤嬤懈怠、宮人失儀者,嚴加整肅,卻不妄加責罰。
她懂得分寸之道,也知人心之險,凡事不過三言兩語,言簡意賅,令人既敬又畏。
後宮中最怕的不是嚴厲,而是偏私,而她,最不偏私。
她對前皇后的嫡子綿寧,一如既往地關懷備至,綿寧幼年時,常喚她「鈕額娘」,如今仍親近如初。
這份胸襟,是旁人學不來的。
嘉慶六年,紫禁城裡張燈結彩,金鳳高懸。
大典那日,百官齊聚,六宮列隊,她身披霞帔鳳袍,頭戴九鳳冠,一步一跪,緩緩登上坤寧宮寶座,鳳印加身。
那一刻,她終於成為了真正的「中宮之主」。
作為皇后,她必須打理六宮、統籌內務、輔佐皇帝,還要維護宮中數百人的衣食秩序。
她每日在景仁宮與儲秀宮之間來回,查帳目、閱奏本、批宮務,忙到深夜不曾休息。
嘉慶雖不似其父那般精於政事,但對她卻極為信任。
朝中大臣奏事涉內廷者,往往要「請中宮裁定」,綿寧生病,她親自侍藥。
她不是鳳凰中最耀眼的那一隻,卻是羽翼最堅韌、飛得最長久的那一隻。
垂簾幕後,定鼎儲君
嘉慶二十五年,皇城傳來噩耗,嘉慶皇帝猝然駕崩,消息自山莊傳回京師,一石激起千層浪。
紫禁城沉入一片凝重之中,內務府連夜進宮稟告,太監奔走,宮門閉鎖,百官靜候遺詔。
宮中嬪妃宮女無不驚恐失措,仿佛一夜間,帝國失去了心臟的跳動。
此時,掌中樞、握六宮、又年屆半百的皇后鈕祜祿氏,聽聞皇帝駕崩,雖神情沉痛,卻未有絲毫慌亂,從壽康宮到皇宮正殿,她一路未言。
皇帝驟亡,繼承人尚未公布,朝堂上下尚未有定策之人。
稍有不慎,便可能釀成儲位之爭,亂起朝野。
按照清朝「家法」,皇帝在生前若已秘密立儲,遺詔會藏於乾清宮「正大光明」匾額之後,亦有副本封入金匣,由親信隨身保管。
但在嘉慶突然崩逝之後,無人知曉密詔何在,太監翻遍了乾清宮、景仁宮、養心殿,皆未有所獲。
群龍無首之際,有人開始低聲議論,「太后有二子,皆出嘉慶,是否……」
聲雖微,卻如風中毒草,極易蔓延成災。
鈕祜祿氏沒有急於召見百官,也沒有將自己的兒子綿愷或綿忻召回宮中,而是命人火速前往承德,尋找皇帝隨身之物。
大臣們心知肚明,若太后有意讓自己的親子繼位,此刻大可下旨「立子承統」,卻並未如此,可見其心志之清明。
兩日後,承德飛馬急傳回金匣密詔,詔中赫然寫明:
「皇次子綿寧,承朕衣缽,繼統大清。」
一錘定音,太后只點頭一言:「照旨。」
那一刻,她將本可據為己有的權力,親手交出,她的兒子未登大位,卻毫無怨言,而她本人,也因此舉,被朝中文武一致稱為「賢后」。
自此,鈕祜祿氏尊為「恭慈皇太后」,徹底走入幕後,卻並未退出政事。
道光皇帝初登大位,雖為嫡子,但政治經驗尚淺,軍國大事仍需請安問策。
鈕祜祿氏每日清晨必起,按時接見皇帝,叮囑之言從不溢美,亦不縱容。
這種分寸,她拿捏得恰到好處。
自此,她不再只是那個曾為公主伴讀的小宮女,也不只是安於王府一隅的側福晉。
她開始參與內廷事務,打理中饋、掌管禮儀,連宮中都傳來了她賢良持家的名聲。
而她的父親恭阿拉,也因女兒之貴,被提拔為從三品官職,一家人總算過上安穩光景。
可這位鈕祜祿氏依舊不驕不躁。
鳳冠加身
乾隆六十年,當年的英武皇帝早已白髮蒼蒼,卻依舊精神矍鑠。
他雖早已決定退位,卻不願捨去「太上皇」的尊號與權力。
彼時的乾隆,雖讓皇子顒琰登基為帝,改元嘉慶,但宮中宮外誰都明白,這座帝國的真正舵手,依舊坐在那座養心殿里。
正是在這個微妙的交接時刻,鈕祜祿氏迎來了人生的又一次躍遷。
嘉慶元年正月初四,皇帝剛剛繼位第四日,便下旨冊封她為「貴妃」。
這道聖旨不是單純的禮數,而是朝廷對她多年來德行的肯定。
而讓這段榮寵更進一步的,是嘉慶二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喪禮。
皇后喜塔臘氏因久病無愈,不幸崩逝,享年不過三十餘,消息傳出,整個內廷哀悼不已。
皇后之位空懸,皇帝需要一位能穩定後宮、替他料理內務的中宮之主,諸妃中,惟鈕祜祿氏最為合適。
這一次,冊立未如往常那般倉促行禮,而是遵循太上皇定下的規制,需守先皇后喪期二十七月後,方可行冊立大典。
於是在嘉慶二年,她先被晉封為「皇貴妃」,暫攝六宮之政,直到嘉慶六年正式立為皇后,移居儲秀宮。
這期間,六宮之中風起雲湧。
皇貴妃位高權重,又年紀不大,朝中有人言她「受太上皇之恩,恩寵深厚」。
宮中也有舊妃暗中譏諷:「出身寒微,焉能掌後宮?」
她聽得多,卻從未回過一句,只以實際行動回應流言。
她每日親自督查各宮膳食衣物,遇嬤嬤懈怠、宮人失儀者,嚴加整肅,卻不妄加責罰。
她懂得分寸之道,也知人心之險,凡事不過三言兩語,言簡意賅,令人既敬又畏。
後宮中最怕的不是嚴厲,而是偏私,而她,最不偏私。
她對前皇后的嫡子綿寧,一如既往地關懷備至,綿寧幼年時,常喚她「鈕額娘」,如今仍親近如初。
這份胸襟,是旁人學不來的。
嘉慶六年,紫禁城裡張燈結彩,金鳳高懸。
大典那日,百官齊聚,六宮列隊,她身披霞帔鳳袍,頭戴九鳳冠,一步一跪,緩緩登上坤寧宮寶座,鳳印加身。
那一刻,她終於成為了真正的「中宮之主」。
作為皇后,她必須打理六宮、統籌內務、輔佐皇帝,還要維護宮中數百人的衣食秩序。
她每日在景仁宮與儲秀宮之間來回,查帳目、閱奏本、批宮務,忙到深夜不曾休息。
嘉慶雖不似其父那般精於政事,但對她卻極為信任。
朝中大臣奏事涉內廷者,往往要「請中宮裁定」,綿寧生病,她親自侍藥。
她不是鳳凰中最耀眼的那一隻,卻是羽翼最堅韌、飛得最長久的那一隻。
垂簾幕後,定鼎儲君
嘉慶二十五年,皇城傳來噩耗,嘉慶皇帝猝然駕崩,消息自山莊傳回京師,一石激起千層浪。
紫禁城沉入一片凝重之中,內務府連夜進宮稟告,太監奔走,宮門閉鎖,百官靜候遺詔。
宮中嬪妃宮女無不驚恐失措,仿佛一夜間,帝國失去了心臟的跳動。
此時,掌中樞、握六宮、又年屆半百的皇后鈕祜祿氏,聽聞皇帝駕崩,雖神情沉痛,卻未有絲毫慌亂,從壽康宮到皇宮正殿,她一路未言。
皇帝驟亡,繼承人尚未公布,朝堂上下尚未有定策之人。
稍有不慎,便可能釀成儲位之爭,亂起朝野。
按照清朝「家法」,皇帝在生前若已秘密立儲,遺詔會藏於乾清宮「正大光明」匾額之後,亦有副本封入金匣,由親信隨身保管。
但在嘉慶突然崩逝之後,無人知曉密詔何在,太監翻遍了乾清宮、景仁宮、養心殿,皆未有所獲。
群龍無首之際,有人開始低聲議論,「太后有二子,皆出嘉慶,是否……」
聲雖微,卻如風中毒草,極易蔓延成災。
鈕祜祿氏沒有急於召見百官,也沒有將自己的兒子綿愷或綿忻召回宮中,而是命人火速前往承德,尋找皇帝隨身之物。
大臣們心知肚明,若太后有意讓自己的親子繼位,此刻大可下旨「立子承統」,卻並未如此,可見其心志之清明。
兩日後,承德飛馬急傳回金匣密詔,詔中赫然寫明:
「皇次子綿寧,承朕衣缽,繼統大清。」
一錘定音,太后只點頭一言:「照旨。」
那一刻,她將本可據為己有的權力,親手交出,她的兒子未登大位,卻毫無怨言,而她本人,也因此舉,被朝中文武一致稱為「賢后」。
自此,鈕祜祿氏尊為「恭慈皇太后」,徹底走入幕後,卻並未退出政事。
道光皇帝初登大位,雖為嫡子,但政治經驗尚淺,軍國大事仍需請安問策。
鈕祜祿氏每日清晨必起,按時接見皇帝,叮囑之言從不溢美,亦不縱容。
這種分寸,她拿捏得恰到好處。
 呂純弘 • 13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9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