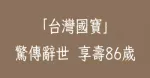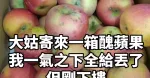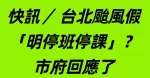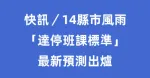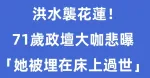1/3
下一頁
晚清一奇才借錢從不花,放箱子裡到期便還,用此套路攢下億萬身家

1/3
晚清一奇才借錢從不花,放箱子裡到期便還,用此套路攢下億萬身家
1890年的上海,南京路燈火通明,黃楚九站在法大馬路的街角,望著對面的西藥鋪出神。
他沒有資本、沒有背景,只有一雙眼睛,能看透人性,一顆心,敢想敢幹。
這位出身寒門的少年,用一個所有人都不理解的「借錢不花」套路,硬生生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商業帝國之路。
借錢不花,到期就還,這究竟是「愚蠢」,還是「精明」?
窮到極致反生妙計
1872年,黃楚九出生於浙江餘姚一個寒門之家。
他的父親是一名靠懸壺濟世勉強餬口的中醫,但在黃楚九十五歲那年,病重離世,留下年幼的黃楚九和母親掙扎求生。
母親略懂醫術,尤其精於祖傳的眼科。
為了餬口,她背著藥箱走街串巷,為鄉鄰診治眼疾。
而黃楚九自幼便跟在母親身邊,耳濡目染中學會了不少基本的診治方法。
生活的艱辛讓他早熟,也讓他不得不放棄書本和課堂。
因無力承擔學費,他很早便輟學,開始獨自謀生。
街頭診病是他賴以為生的手段,卻遠遠不是他願意困守一生的歸宿,他要翻身,要另尋出路。
19世紀末,上海被譽為「東方巴黎」,城市的繁華背後,是層層疊疊的機會和危機。
也正是在這一時期,黃楚九帶著母親背井離鄉,來到了這裡,他依舊是沿襲舊業,在街頭擺攤替人治眼病。
不同的是,這座城市比家鄉更喧囂,也更冷漠,他的攤子夾在西藥房與洋行之間,顯得格外不起眼。
隔壁那家掛著「英美藥局」招牌的店鋪,卻門庭若市、絡繹不絕。
他開始意識到,中醫雖然博大精深,但在追求「快效」的上海人面前,顯得力不從心。
那些穿西裝、戴禮帽的人並不在意藥的出處,只在意藥效有多快、病能不能馬上好。
黃楚九沒有立刻下判斷,他開始悄悄觀察,甚至裝作病人,走進那些西藥房。
他仔細端詳藥瓶上的英文標籤,翻看櫃檯邊堆放的外國醫學期刊。
他的眼裡不只是看到藥,他看到了一整個被國人忽視的巨大市場。
但問題也來了,他是個三無人員,無資金、無技術、無背景。
這三座大山,足以把千千萬萬個「想改變命運」的人壓得喘不過氣來。
黃楚九的聰明之處這就體現出來了。
他從不正面撞牆,而是繞過硬碰硬的路徑,另闢蹊徑。
他很快就想到了一個所有人都不會想到的「辦法」,借錢。
可借錢就能解決問題嗎?他根本沒任何產業可作為抵押,也沒有可期待的盈利項目。
但他還真就做到了。
頭一回,他只是找一位關係稍熟的商販,開口借了幾兩銀子,說是「周轉生意」,這錢不多,人家就借給他了。
拿到錢後,他沒有花一分,而是把銀子放進自家角落的一個舊木箱裡,鎖好。
等約定時間一到,便原封不動地將本金和利息一併歸還。
又一會,他找了另一位富戶,又借了一點,同樣,他還是一分未動,等時間一到照舊歸還。
三次、四次、五次……在這些看似「毫無意義」的操作中,黃楚九慢慢在上海的借貸圈子中傳出一個名聲,「這小子,講信用。」
借來的錢就像是魚餌,他從不啃咬,卻用一串串準時歸還的記錄,釣來了最難得的「信任」。
到了後來,不止是普通商販,就連一些銀行職員都主動向他推薦「小額貸款」項目。
他越借越多,從幾兩到十幾兩、再到上百銀元,但始終如一,放箱子裡,到點歸還,分毫不差。
這套看似愚蠢的「空箱計」,卻積攢了比金子還要珍貴的信用。
銀子存箱,不過是一種「行為演出」,而他真正想獲得的,是未來無數資本願意主動送上門的那一天。
箱中生金,名動上海
在那個「錢過一手便蒸發」的動盪年代裡,能夠按時還錢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那些曾經將錢借給他的人起初疑慮重重,後來逐漸放心,再後來則搶著將更多的錢遞到他面前。
他們不再追問「你拿去幹嘛」,因為他們已經知道,不論錢從哪來、到哪去,只要是借給黃楚九,就像存進了銀行。
有一天,一家老牌銀號的掌柜甚至專門找上門來:
「黃先生,若有需要,我們願意無抵押貸款。」
此言一出,黃楚九心中頓時有了一個久藏已久的計劃,該動用了。
1890年的上海法大馬路上,西洋建築和中式招牌並肩而立,叫賣聲與駁雜方言交織著這座城市的喧囂。
就在這塊最繁華、最具現代氣息的地段,黃楚九用一紙借據從銀行貸得了三千銀元,租下了一間寬敞門面,掛牌「中法藥房」。
為了打破日本人壟斷的「仁丹」市場,他決定親手調配出一種同類卻更優的藥丸,這藥丸最終被命名為,「龍虎人丹」。
這個名字大有深意,「仁丹」是當時日本東亞公司出品的常用藥,標榜清熱解暑、止暈止嘔,幾乎壟斷了上海灘的藥品市場。
1890年的上海,南京路燈火通明,黃楚九站在法大馬路的街角,望著對面的西藥鋪出神。
他沒有資本、沒有背景,只有一雙眼睛,能看透人性,一顆心,敢想敢幹。
這位出身寒門的少年,用一個所有人都不理解的「借錢不花」套路,硬生生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商業帝國之路。
借錢不花,到期就還,這究竟是「愚蠢」,還是「精明」?
窮到極致反生妙計
1872年,黃楚九出生於浙江餘姚一個寒門之家。
他的父親是一名靠懸壺濟世勉強餬口的中醫,但在黃楚九十五歲那年,病重離世,留下年幼的黃楚九和母親掙扎求生。
母親略懂醫術,尤其精於祖傳的眼科。
為了餬口,她背著藥箱走街串巷,為鄉鄰診治眼疾。
而黃楚九自幼便跟在母親身邊,耳濡目染中學會了不少基本的診治方法。
生活的艱辛讓他早熟,也讓他不得不放棄書本和課堂。
因無力承擔學費,他很早便輟學,開始獨自謀生。
街頭診病是他賴以為生的手段,卻遠遠不是他願意困守一生的歸宿,他要翻身,要另尋出路。
19世紀末,上海被譽為「東方巴黎」,城市的繁華背後,是層層疊疊的機會和危機。
也正是在這一時期,黃楚九帶著母親背井離鄉,來到了這裡,他依舊是沿襲舊業,在街頭擺攤替人治眼病。
不同的是,這座城市比家鄉更喧囂,也更冷漠,他的攤子夾在西藥房與洋行之間,顯得格外不起眼。
隔壁那家掛著「英美藥局」招牌的店鋪,卻門庭若市、絡繹不絕。
他開始意識到,中醫雖然博大精深,但在追求「快效」的上海人面前,顯得力不從心。
那些穿西裝、戴禮帽的人並不在意藥的出處,只在意藥效有多快、病能不能馬上好。
黃楚九沒有立刻下判斷,他開始悄悄觀察,甚至裝作病人,走進那些西藥房。
他仔細端詳藥瓶上的英文標籤,翻看櫃檯邊堆放的外國醫學期刊。
他的眼裡不只是看到藥,他看到了一整個被國人忽視的巨大市場。
但問題也來了,他是個三無人員,無資金、無技術、無背景。
這三座大山,足以把千千萬萬個「想改變命運」的人壓得喘不過氣來。
黃楚九的聰明之處這就體現出來了。
他從不正面撞牆,而是繞過硬碰硬的路徑,另闢蹊徑。
他很快就想到了一個所有人都不會想到的「辦法」,借錢。
可借錢就能解決問題嗎?他根本沒任何產業可作為抵押,也沒有可期待的盈利項目。
但他還真就做到了。
頭一回,他只是找一位關係稍熟的商販,開口借了幾兩銀子,說是「周轉生意」,這錢不多,人家就借給他了。
拿到錢後,他沒有花一分,而是把銀子放進自家角落的一個舊木箱裡,鎖好。
等約定時間一到,便原封不動地將本金和利息一併歸還。
又一會,他找了另一位富戶,又借了一點,同樣,他還是一分未動,等時間一到照舊歸還。
三次、四次、五次……在這些看似「毫無意義」的操作中,黃楚九慢慢在上海的借貸圈子中傳出一個名聲,「這小子,講信用。」
借來的錢就像是魚餌,他從不啃咬,卻用一串串準時歸還的記錄,釣來了最難得的「信任」。
到了後來,不止是普通商販,就連一些銀行職員都主動向他推薦「小額貸款」項目。
他越借越多,從幾兩到十幾兩、再到上百銀元,但始終如一,放箱子裡,到點歸還,分毫不差。
這套看似愚蠢的「空箱計」,卻積攢了比金子還要珍貴的信用。
銀子存箱,不過是一種「行為演出」,而他真正想獲得的,是未來無數資本願意主動送上門的那一天。
箱中生金,名動上海
在那個「錢過一手便蒸發」的動盪年代裡,能夠按時還錢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那些曾經將錢借給他的人起初疑慮重重,後來逐漸放心,再後來則搶著將更多的錢遞到他面前。
他們不再追問「你拿去幹嘛」,因為他們已經知道,不論錢從哪來、到哪去,只要是借給黃楚九,就像存進了銀行。
有一天,一家老牌銀號的掌柜甚至專門找上門來:
「黃先生,若有需要,我們願意無抵押貸款。」
此言一出,黃楚九心中頓時有了一個久藏已久的計劃,該動用了。
1890年的上海法大馬路上,西洋建築和中式招牌並肩而立,叫賣聲與駁雜方言交織著這座城市的喧囂。
就在這塊最繁華、最具現代氣息的地段,黃楚九用一紙借據從銀行貸得了三千銀元,租下了一間寬敞門面,掛牌「中法藥房」。
為了打破日本人壟斷的「仁丹」市場,他決定親手調配出一種同類卻更優的藥丸,這藥丸最終被命名為,「龍虎人丹」。
這個名字大有深意,「仁丹」是當時日本東亞公司出品的常用藥,標榜清熱解暑、止暈止嘔,幾乎壟斷了上海灘的藥品市場。
 呂純弘 • 1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