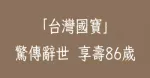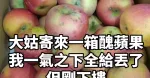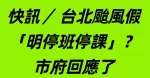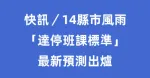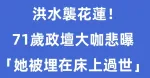1/4
下一頁
大宋居然糟蹋了這麼牛X的人物

1/4
大宋居然糟蹋了這麼牛X的人物
靖康元年(1126年)正月,金兵長驅直入,攻占相州(今河南安陽),距離開封不過咫尺之遙。
宋徽宗內禪後,從小不愛嬉戲遊玩、才能平平的老實人宋欽宗,從他老爸手中接過了皇位這個燙手山芋,終日惶恐,無法安心過新年。
宰相李綱給了他安全感。
城外戰況緊急,李綱招募敢死之士2000人,身先士卒,與金人鏖戰於京城西北。之後,刺血上書勸說宋徽宗退位的李綱,又擔負起保衛京城的重任,還把打算棄城而逃的宋欽宗拉了回來。
宋欽宗聽說金兵渡河,本來撒腿就要跑,禁軍將士都備好鞍馬,甚至把太廟供奉的皇帝牌位也請了出來,一行人在清晨時偷偷摸摸地整裝待發。
李綱進宮見此情景,對將士們厲聲說道:「爾等願以死守宗廟乎?」
將士們不願當逃兵,高喊:「我等願意死守!不在此,將去何處?」
▲「靖康元年春正月,金人犯京師,軍於城西北。」圖源:影視劇照
這仗不好打,卻還有得打。
李綱入殿,對宋欽宗說:「陛下昨天跟臣說要留下,今天又要跑路,這是為何?六軍將士的父母妻兒都在京城,不願離去,萬一中途失散,誰來當您的保鏢?況且敵人的騎兵已經逼近,若他們知道陛下車駕出城未遠,快馬加鞭前去追趕,該如何抵擋?」
宋欽宗聽到出城更危險,小心臟有點受不了,只好留在城中。但朝中主和派依舊畏金如虎,處處對李綱形成掣肘,還派人出使金營,以納幣、割地、送人質為條件,請金人退兵。
李綱身陷主和派圍攻時,另一個主戰派大臣宗澤也來到了開封。
不久後,在主和派的舉薦下,宗澤被任命為「和議使」。臨行前他對小夥伴們說:「我這一去,就不能活著回來了。」
眾人感到詫異,問他這是為何。
宗澤正氣凜然地回答道:「敵人若知悔改,帶兵撤離自然是好事。否則,我怎麼可能向金人卑躬屈膝,有辱使命呢!」
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宋欽宗,主和派才知,這個使者根本就沒想替朝廷議和,而是鐵了心要和金人搏命,這不得談崩了。趁著車馬還沒出發,宋欽宗趕緊把宗澤撤下來,改派他出知磁州(今河北磁縣)。
李綱與宗澤,這兩位鐵骨錚錚的的主戰派,在國家危難之際同時趕赴前線。
他們的命運從此與大宋一落千丈的國運交織在一起,餘生陷入有心報國、無力回天的無盡愁苦之中。
金人兵臨開封城下,李綱將城中兵力重新布防,命弓箭手猛射金兵,放火焚燒攻城雲梯,等待各路勤王軍隊陸續到來。
城外,各路宋軍集結,號稱20萬。城中軍民士氣大振,同仇敵愾,還有李綱主持大局,可北宋還是沒有逃過滅亡的命運,甚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恥辱。
南宋的朱熹評價靖康年間朝政時,用了這四個字——「無一是處」。
很多人常認為,宋欽宗就是個背黑鍋的,如果沒有他爹宋徽宗把國家折騰得烏煙瘴氣,北宋朝廷也不會迅速崩潰。實際上,宋欽宗這個亡國之君,對北宋覆滅也有不少責任,是他自己把取勝的籌碼全給賠進去了。
曾經有一個李綱在宋欽宗面前,他沒有好好珍惜。
在指揮開封保衛戰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,李綱兩度被貶,他提出的計策,宋欽宗不願採納,失利後卻還要追究他的責任。
起初,李綱認為金人貪婪無厭,戰鬥力極強,宋軍應該堅壁固守,等到金人食盡力疲時,再出兵收復失地。「縱其北歸,半渡而擊之」,這就是必勝之道。
但是,宋欽宗卻一心想用20萬大軍速戰速決,執意命各路軍隊出戰,偷襲金營。結果,宋軍劫寨失敗,主和派把出師敗績的罪名推到李綱等主戰派身上,李綱因此被罷免官職。
李綱指揮作戰時,金人不敢貿然出擊,聽說李綱被罷官,他們當天就派出一支騎兵到城下耀武揚威,氣焰囂張。
城中宋朝臣民的表現比金人還要激烈,太學生陳東叫來上百名同學伏闕上書,掀起一場大規模抗議運動。聞風而來的軍民多達十餘萬人,集結於宮門外為李綱伸冤,直言李綱是唯一能承擔天下重任的人,主和派大臣儘是「庸繆不才,忌疾賢能」之輩。
憤怒的群眾毀壞了宮門外的欄杆,甚至朝主和派大臣投擲瓦礫,之後還打死了幾個宦官。當有人指責他們要挾天子時,太學生們高聲答道:「以忠義脅天子,不逾於奸佞脅之乎?」
之後,宋欽宗急命李綱官復原職,並一起登上高樓與百姓見面,才漸漸平息眾怒。
在這場北宋滅亡前夕的愛國請願運動中,抗議者的思想高度可謂超前,他們不顧所謂的君臣大義,寧死也要支持忠心報國的李綱復職。這是一種真正的愛國精神。
但身處漩渦中心的李綱,也因此引起宋朝皇帝忌憚。
在李綱復職次日,宋欽宗頒布命令,說:「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為名者,意在做亂,今後如更有似此之人,即與收捉,並從軍法斬訖奏聞。」
這是說,今後再有群眾抗議,直接處死。
李綱復出後,再次整軍備戰,痛擊金兵,形勢對城外的金人愈發不利。勝利的天平一度向宋軍傾斜,進退失據的金兵,終於在次月解圍而去。
宋欽宗看金人走了,有點兒飄,主和派大臣趁機散布流言,說李綱早就有意鼓動太學生,威脅皇帝重用自己。在朝中奸佞小人的打壓下,正義的聲音再度被淹沒。
當時開封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謠:「城門閉,言路開;城門開,言路閉。」
北宋朝廷一片混亂,僅僅過了幾個月,金兵就捲土重來,于靖康元年秋攻陷了堅守八個多月的軍事重鎮太原,又一次劍指汴京,陰霾籠罩在黃河兩岸。
此時,李綱卻已被貶出朝。他被宋欽宗派往河北、河東解圍,實際上無兵無錢,戰敗後被貶到南方。李綱離京前為朝廷籌劃的抗金之策,也被主和派全盤否定。
李綱前腳剛走,宋欽宗受投降派蠱惑,將他所徵調的軍隊罷去一半,尤其是罷四川、福建、廣東、荊湖諸路正規軍與京西諸州的非正規軍,取消錢糧犒賞的費用,完全就是「送人頭」行為。
離京不過幾天的李綱得知後大驚,連忙上書反對。其中說到,主和派認為四川等地路途遙遠,但徵發之詔四月就已下達,現在遠方之兵都在路上,如果以寸紙之書讓他們回去,朝廷如何取信於天下?臣擔心日後再有號召,天下無應者矣!
果不其然,金兵再次兵臨開封城下,偏遠之地響應朝廷號召的勤王之兵寥寥無幾。
▲李綱(1083-1140)。圖源:網絡
宋廷不斷派出使者求和,卻無法抵擋金兵進軍的步伐。金人根本沒把屈辱求和的北宋君臣放在眼裡,說:「待汝家議論定時,我已過河矣。」
另一邊,早已看出議和並非救國之策的宗澤,正帶領十幾個老弱士卒前往磁州任職,那是抗金的第一線。一路上,臨危不懼的宗澤寫下了《早發》一詩:
傘幄垂垂馬踏沙,水長山遠路多花。
眼中形勢胸中策,緩步徐行靜不嘩。
這一年,宗澤已年近七旬,他招募義勇,發動民眾修繕城牆,製造兵器。磁州一帶抗金形勢一片大好,宗澤為此上書道:「邢、洺、磁、趙、相五州,各蓄精兵二萬,敵攻一郡,則四郡皆應,是一郡之兵,常有十萬人也。」
但朝廷仍然是主和派占了上風,宋欽宗派出宋徽宗第九子、康王趙構再度出使金營議和。
趙構路過磁州時,宗澤叩拜迎接,勸諫道:「金人不過是用花言巧語誘騙我們前去議和,他們的軍隊已經打過來了,再去金營還有什麼可談的,請康王不要去了!」
趙構很聰明,他也聽說金兵已經渡河,不願自投羅網,於是掉了個頭,後來一邊受宋欽宗冊封,打著兵馬大元帥的旗號聚集潰軍,一邊跑到濟州(今山東巨野)安頓下來,不敢與金兵正面交鋒。宗澤多次苦勸他直趨澶淵,收復失地,解京城之圍,趙構卻無動於衷。
宗澤只好孤軍奮戰,向開封進軍。宗澤率軍出征後,一路和金兵打了十三場仗,全部獲勝,將士們毫不畏懼金兵強悍的戰鬥力。
國難當頭,宗澤一面寫信請趙構會師京城,一面聯絡其他宋軍,繼續向開封挺進。他鼓舞手下將士,說:「現在進退都是死,我們必須死裡求生!」
李綱與宗澤的奮戰,還是無法阻止汴京陷落。
宋欽宗向金人遞上降書後,滿城君臣百姓如羊入虎口,儘是悲泣之聲。
靖康二年(1127年),金人縱火焚城,燒殺擄掠,挾持徽欽二帝、宗室、妃嬪、大臣等三千多人北歸。
宗澤得知這一消息,立即率領大軍抄近路趕到大名(今河北大名縣),想聯合各軍過河堵住金兵的歸路,將二帝搶回來。
可當他到達時,各路軍隊竟然沒有一支前來勤王,宗澤孤掌難鳴,只好望河興嘆,眼見金人帶著「戰利品」遠去。北宋俘虜到了北方苦寒之地,「男十存四,女十存七」,無數人慘遭蹂躪侮辱,倒斃路旁。
這,就是靖康之變。北宋,滅亡。
老當益壯的宗澤,深深感受到一種無力感,而這種不甘與悲憤,成為其短暫的抗金生涯中唯一的基調。
吃瓜看戲的趙構成了大贏家。
21歲的趙構,從孟太后(北宋哲宗皇后)派出的使者手中接過刻有篆文「大宋受命之寶」的玉璽,在南京應天府(今河南商丘)即位稱帝,改元建炎,重建政權,史稱南宋。
宋高宗趙構為了樹立威望,即位後不得不起用主戰派的李綱為相。他還寫了封信給受命回朝的李綱:「方今天下生民遭此劫難,只有閣下這樣學窮天人、忠貫金石的大臣輔佐朕,才能符合蒼生的期望。」
趙構的親信黃潛善、汪伯彥對這一安排極為不滿,這兩位都是「無進攻之志」的主和派,且自以為對宋高宗有「攀附之勞」,怎麼說也得討個宰相噹噹。
黃、汪二人,成了李綱、宗澤抗金的阻礙,而他們背後的老闆趙構,也是一個耳根子軟的懦弱之徒。
建炎元年(1127年),李綱出任宰相後,為趙構呈上「議國是」等十事,認為當務之急是防禦金人再次南侵。他與主和派勢不兩立,敢於當面與皇帝的寵臣黃、汪抬槓,這股忠直耿介的氣度讓他與宋高宗漸行漸遠。
李綱前來行在拜見高宗時,趙構知道他跟主和派鬧矛盾,就讓黃潛善負責設宴款待,並由汪伯彥等人陪同,希望他們盡釋前嫌,修復一下關係。沒有什麼是一頓飯不能解決的,如果有,那就兩頓。
可是李綱不按套路出牌,他見過趙構後,上奏請辭此宴,直接回家,把黃潛善等朝中大臣直接晾在大門外,也不打聲招呼。
汪、黃早已備好筵席,等了大半天也沒見著李綱人影,得知真相後怒不可遏,從此玩了命整李綱。
趙構一即位,之前擔任其副元帥的宗澤也前往拜見,向高宗陳述抗金大計,說到激動時不禁老淚縱橫,在一旁的李綱也為之動容。
一天,李綱在朝見時與宗澤偶遇,有過一番談話,他們談及國事,為之心痛不已,也為抗金大業慷慨激昂。當時,開封府缺一名獨當一面的大臣駐守,李綱就向高宗極力推薦宗澤:「綏復舊都,非宗澤不可。」
趙構早想著重用宗澤,李綱也欲留他共同主持大局,但是以黃潛善、汪伯彥為首的主和派大臣屢屢從中作梗。最後,高宗只是授宗澤以龍圖閣學士、知襄陽府,讓他去建設大後方。
李綱立馬察覺此事不對勁,便一再奏請擢宗澤為開封府尹、東京留守,大力支持其對京城的防禦。
這些「糟老頭子」犟得很,趙構自知拗不過,只好同意。
孤獨的宗澤,在主和派輕蔑的眼光中,來到那座已經沒有皇帝的都城。
開封不久前慘遭金兵劫掠,盜賊蜂起,人心惶惶,城中殘破不堪,「凍餒死者十五、六」,早已看不出一絲《清明上河圖》中那盛世繁榮的氣象。
同樣孤立的李綱,在朝中不斷受到黃、汪等黨羽的攻擊。
有人說李綱,「名浮於實,而有震主之威,不可以相。」還有人老調重彈,用之前北宋大臣的言論抨擊他:「為金人所惡,不宜為相。」
李綱與宗澤有共同主張,他們一人在朝,一人在汴,艱難支撐起抗金的大旗。
他們都善於利用河北、河東等地民兵。
當時,各地義兵興起,打著勤王的旗號,卻各懷心思,難以統一調度。但朝廷眼中的這些「匪」「寇」兵力雄厚,是李綱與宗澤一心爭取的對象。
淮南的杜用,山東的李昱,襄陽的李孝忠,都被李綱調兵遣將一一討平,降者多達十餘萬,歸於諸將帳下,聽候調遣,構成一道橫跨數州的防線,只待渡河討伐金兵。
京西、淮南、兩河一帶的「草頭王」們也在宗澤愛國精神的感召下,紛紛加入匡扶宋室的隊伍。
濮州義軍的首領王善,自稱手下有數十萬之眾,兵車萬乘,本來不給宗澤好臉色看,還想出兵占領汴京。
宗澤聽聞此事,親自前去勸降,單騎入營與王善相見,請他加入抗金大軍,說:「朝廷正當危難之時,如果有一兩位如你這樣的人,豈還會有敵患?今日就是立功的好時機,機不可失啊。」
王善一看,宗澤年近七旬,還一心為國為民,極富誠意,對他佩服不已,二話不說,解甲歸降。
壽春人丁進,江湖人稱「丁一箭」,聚眾數萬人,聽聞宗澤的威名,帶兵前往京城近郊求見。
宗澤的部下都擔心有詐,宗澤卻說:「精誠所至,金石為開,何況是人呢?」
丁進到後,宗澤親自接見,像對待老部下一樣與他親切交談。丁進十分感動,當即請宗澤前去視察他的部隊。宗澤毫不懷疑,第二天就去慰問了丁進的軍隊。
從此,丁進所部歸入宗澤麾下,成為保衛汴京的一支生力軍。如果發現隊伍中有人懷有二心,丁進會果斷地將其斬殺。
除此之外,還有外號「沒角牛」的楊進、李貴、王大郎、王再興等各自擁兵割據一方,宗澤曉以大義,將他們一一招降。
李、宗二人對主戰派的同志,也都是知人善任。
李綱舉薦了張所、傅亮等主戰派,此二人分別被任命為河北路招撫使與河東路招撫使。
張所在北宋當過御史,宋朝向金朝割地求和時,他主張招募河北民兵救援京城,後來黃潛善被高宗重用後,他又上疏直言黃潛善姦邪誤國,因此被貶到江州。這些主戰派一個個都脾氣火爆。
得到李綱提拔後,張所來到河北招攬豪傑,整頓軍備。一個因越職言事而被逐出軍營的青年,在此時來到河北投奔張所,後來歸於宗澤帳下。
他,就是岳飛。
岳飛只是一個低級軍官,敢於說真話,此前上書論事,惹禍上身。
他竟然譴責「黃潛善、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,奉車駕日益南,恐不足系中原之望」,還義正辭嚴地請高宗「親率六軍北渡,則將士作氣,中原可復」。
這樣一個刺兒頭,深得宗澤器重。
有一次,岳飛觸犯了軍法,本來要嚴加處置。宗澤一見到他,交談之後,發現他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將才。
正值金人入侵汜水,宗澤給了岳飛將功補過的機會,讓他帶五百名騎兵作為先鋒部隊出戰。
岳飛初出茅廬,就盡顯軍事奇才,在這次遭遇戰中痛擊金軍。岳飛凱旋後,宗澤赦免了他的罪,並升他為統制,年輕的岳飛由此成名。
靖康元年(1126年)正月,金兵長驅直入,攻占相州(今河南安陽),距離開封不過咫尺之遙。
宋徽宗內禪後,從小不愛嬉戲遊玩、才能平平的老實人宋欽宗,從他老爸手中接過了皇位這個燙手山芋,終日惶恐,無法安心過新年。
宰相李綱給了他安全感。
城外戰況緊急,李綱招募敢死之士2000人,身先士卒,與金人鏖戰於京城西北。之後,刺血上書勸說宋徽宗退位的李綱,又擔負起保衛京城的重任,還把打算棄城而逃的宋欽宗拉了回來。
宋欽宗聽說金兵渡河,本來撒腿就要跑,禁軍將士都備好鞍馬,甚至把太廟供奉的皇帝牌位也請了出來,一行人在清晨時偷偷摸摸地整裝待發。
李綱進宮見此情景,對將士們厲聲說道:「爾等願以死守宗廟乎?」
將士們不願當逃兵,高喊:「我等願意死守!不在此,將去何處?」
▲「靖康元年春正月,金人犯京師,軍於城西北。」圖源:影視劇照
這仗不好打,卻還有得打。
李綱入殿,對宋欽宗說:「陛下昨天跟臣說要留下,今天又要跑路,這是為何?六軍將士的父母妻兒都在京城,不願離去,萬一中途失散,誰來當您的保鏢?況且敵人的騎兵已經逼近,若他們知道陛下車駕出城未遠,快馬加鞭前去追趕,該如何抵擋?」
宋欽宗聽到出城更危險,小心臟有點受不了,只好留在城中。但朝中主和派依舊畏金如虎,處處對李綱形成掣肘,還派人出使金營,以納幣、割地、送人質為條件,請金人退兵。
李綱身陷主和派圍攻時,另一個主戰派大臣宗澤也來到了開封。
不久後,在主和派的舉薦下,宗澤被任命為「和議使」。臨行前他對小夥伴們說:「我這一去,就不能活著回來了。」
眾人感到詫異,問他這是為何。
宗澤正氣凜然地回答道:「敵人若知悔改,帶兵撤離自然是好事。否則,我怎麼可能向金人卑躬屈膝,有辱使命呢!」
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宋欽宗,主和派才知,這個使者根本就沒想替朝廷議和,而是鐵了心要和金人搏命,這不得談崩了。趁著車馬還沒出發,宋欽宗趕緊把宗澤撤下來,改派他出知磁州(今河北磁縣)。
李綱與宗澤,這兩位鐵骨錚錚的的主戰派,在國家危難之際同時趕赴前線。
他們的命運從此與大宋一落千丈的國運交織在一起,餘生陷入有心報國、無力回天的無盡愁苦之中。
金人兵臨開封城下,李綱將城中兵力重新布防,命弓箭手猛射金兵,放火焚燒攻城雲梯,等待各路勤王軍隊陸續到來。
城外,各路宋軍集結,號稱20萬。城中軍民士氣大振,同仇敵愾,還有李綱主持大局,可北宋還是沒有逃過滅亡的命運,甚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恥辱。
南宋的朱熹評價靖康年間朝政時,用了這四個字——「無一是處」。
很多人常認為,宋欽宗就是個背黑鍋的,如果沒有他爹宋徽宗把國家折騰得烏煙瘴氣,北宋朝廷也不會迅速崩潰。實際上,宋欽宗這個亡國之君,對北宋覆滅也有不少責任,是他自己把取勝的籌碼全給賠進去了。
曾經有一個李綱在宋欽宗面前,他沒有好好珍惜。
在指揮開封保衛戰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,李綱兩度被貶,他提出的計策,宋欽宗不願採納,失利後卻還要追究他的責任。
起初,李綱認為金人貪婪無厭,戰鬥力極強,宋軍應該堅壁固守,等到金人食盡力疲時,再出兵收復失地。「縱其北歸,半渡而擊之」,這就是必勝之道。
但是,宋欽宗卻一心想用20萬大軍速戰速決,執意命各路軍隊出戰,偷襲金營。結果,宋軍劫寨失敗,主和派把出師敗績的罪名推到李綱等主戰派身上,李綱因此被罷免官職。
李綱指揮作戰時,金人不敢貿然出擊,聽說李綱被罷官,他們當天就派出一支騎兵到城下耀武揚威,氣焰囂張。
城中宋朝臣民的表現比金人還要激烈,太學生陳東叫來上百名同學伏闕上書,掀起一場大規模抗議運動。聞風而來的軍民多達十餘萬人,集結於宮門外為李綱伸冤,直言李綱是唯一能承擔天下重任的人,主和派大臣儘是「庸繆不才,忌疾賢能」之輩。
憤怒的群眾毀壞了宮門外的欄杆,甚至朝主和派大臣投擲瓦礫,之後還打死了幾個宦官。當有人指責他們要挾天子時,太學生們高聲答道:「以忠義脅天子,不逾於奸佞脅之乎?」
之後,宋欽宗急命李綱官復原職,並一起登上高樓與百姓見面,才漸漸平息眾怒。
在這場北宋滅亡前夕的愛國請願運動中,抗議者的思想高度可謂超前,他們不顧所謂的君臣大義,寧死也要支持忠心報國的李綱復職。這是一種真正的愛國精神。
但身處漩渦中心的李綱,也因此引起宋朝皇帝忌憚。
在李綱復職次日,宋欽宗頒布命令,說:「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為名者,意在做亂,今後如更有似此之人,即與收捉,並從軍法斬訖奏聞。」
這是說,今後再有群眾抗議,直接處死。
李綱復出後,再次整軍備戰,痛擊金兵,形勢對城外的金人愈發不利。勝利的天平一度向宋軍傾斜,進退失據的金兵,終於在次月解圍而去。
宋欽宗看金人走了,有點兒飄,主和派大臣趁機散布流言,說李綱早就有意鼓動太學生,威脅皇帝重用自己。在朝中奸佞小人的打壓下,正義的聲音再度被淹沒。
當時開封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謠:「城門閉,言路開;城門開,言路閉。」
北宋朝廷一片混亂,僅僅過了幾個月,金兵就捲土重來,于靖康元年秋攻陷了堅守八個多月的軍事重鎮太原,又一次劍指汴京,陰霾籠罩在黃河兩岸。
此時,李綱卻已被貶出朝。他被宋欽宗派往河北、河東解圍,實際上無兵無錢,戰敗後被貶到南方。李綱離京前為朝廷籌劃的抗金之策,也被主和派全盤否定。
李綱前腳剛走,宋欽宗受投降派蠱惑,將他所徵調的軍隊罷去一半,尤其是罷四川、福建、廣東、荊湖諸路正規軍與京西諸州的非正規軍,取消錢糧犒賞的費用,完全就是「送人頭」行為。
離京不過幾天的李綱得知後大驚,連忙上書反對。其中說到,主和派認為四川等地路途遙遠,但徵發之詔四月就已下達,現在遠方之兵都在路上,如果以寸紙之書讓他們回去,朝廷如何取信於天下?臣擔心日後再有號召,天下無應者矣!
果不其然,金兵再次兵臨開封城下,偏遠之地響應朝廷號召的勤王之兵寥寥無幾。
▲李綱(1083-1140)。圖源:網絡
宋廷不斷派出使者求和,卻無法抵擋金兵進軍的步伐。金人根本沒把屈辱求和的北宋君臣放在眼裡,說:「待汝家議論定時,我已過河矣。」
另一邊,早已看出議和並非救國之策的宗澤,正帶領十幾個老弱士卒前往磁州任職,那是抗金的第一線。一路上,臨危不懼的宗澤寫下了《早發》一詩:
傘幄垂垂馬踏沙,水長山遠路多花。
眼中形勢胸中策,緩步徐行靜不嘩。
這一年,宗澤已年近七旬,他招募義勇,發動民眾修繕城牆,製造兵器。磁州一帶抗金形勢一片大好,宗澤為此上書道:「邢、洺、磁、趙、相五州,各蓄精兵二萬,敵攻一郡,則四郡皆應,是一郡之兵,常有十萬人也。」
但朝廷仍然是主和派占了上風,宋欽宗派出宋徽宗第九子、康王趙構再度出使金營議和。
趙構路過磁州時,宗澤叩拜迎接,勸諫道:「金人不過是用花言巧語誘騙我們前去議和,他們的軍隊已經打過來了,再去金營還有什麼可談的,請康王不要去了!」
趙構很聰明,他也聽說金兵已經渡河,不願自投羅網,於是掉了個頭,後來一邊受宋欽宗冊封,打著兵馬大元帥的旗號聚集潰軍,一邊跑到濟州(今山東巨野)安頓下來,不敢與金兵正面交鋒。宗澤多次苦勸他直趨澶淵,收復失地,解京城之圍,趙構卻無動於衷。
宗澤只好孤軍奮戰,向開封進軍。宗澤率軍出征後,一路和金兵打了十三場仗,全部獲勝,將士們毫不畏懼金兵強悍的戰鬥力。
國難當頭,宗澤一面寫信請趙構會師京城,一面聯絡其他宋軍,繼續向開封挺進。他鼓舞手下將士,說:「現在進退都是死,我們必須死裡求生!」
李綱與宗澤的奮戰,還是無法阻止汴京陷落。
宋欽宗向金人遞上降書後,滿城君臣百姓如羊入虎口,儘是悲泣之聲。
靖康二年(1127年),金人縱火焚城,燒殺擄掠,挾持徽欽二帝、宗室、妃嬪、大臣等三千多人北歸。
宗澤得知這一消息,立即率領大軍抄近路趕到大名(今河北大名縣),想聯合各軍過河堵住金兵的歸路,將二帝搶回來。
可當他到達時,各路軍隊竟然沒有一支前來勤王,宗澤孤掌難鳴,只好望河興嘆,眼見金人帶著「戰利品」遠去。北宋俘虜到了北方苦寒之地,「男十存四,女十存七」,無數人慘遭蹂躪侮辱,倒斃路旁。
這,就是靖康之變。北宋,滅亡。
老當益壯的宗澤,深深感受到一種無力感,而這種不甘與悲憤,成為其短暫的抗金生涯中唯一的基調。
吃瓜看戲的趙構成了大贏家。
21歲的趙構,從孟太后(北宋哲宗皇后)派出的使者手中接過刻有篆文「大宋受命之寶」的玉璽,在南京應天府(今河南商丘)即位稱帝,改元建炎,重建政權,史稱南宋。
宋高宗趙構為了樹立威望,即位後不得不起用主戰派的李綱為相。他還寫了封信給受命回朝的李綱:「方今天下生民遭此劫難,只有閣下這樣學窮天人、忠貫金石的大臣輔佐朕,才能符合蒼生的期望。」
趙構的親信黃潛善、汪伯彥對這一安排極為不滿,這兩位都是「無進攻之志」的主和派,且自以為對宋高宗有「攀附之勞」,怎麼說也得討個宰相噹噹。
黃、汪二人,成了李綱、宗澤抗金的阻礙,而他們背後的老闆趙構,也是一個耳根子軟的懦弱之徒。
建炎元年(1127年),李綱出任宰相後,為趙構呈上「議國是」等十事,認為當務之急是防禦金人再次南侵。他與主和派勢不兩立,敢於當面與皇帝的寵臣黃、汪抬槓,這股忠直耿介的氣度讓他與宋高宗漸行漸遠。
李綱前來行在拜見高宗時,趙構知道他跟主和派鬧矛盾,就讓黃潛善負責設宴款待,並由汪伯彥等人陪同,希望他們盡釋前嫌,修復一下關係。沒有什麼是一頓飯不能解決的,如果有,那就兩頓。
可是李綱不按套路出牌,他見過趙構後,上奏請辭此宴,直接回家,把黃潛善等朝中大臣直接晾在大門外,也不打聲招呼。
汪、黃早已備好筵席,等了大半天也沒見著李綱人影,得知真相後怒不可遏,從此玩了命整李綱。
趙構一即位,之前擔任其副元帥的宗澤也前往拜見,向高宗陳述抗金大計,說到激動時不禁老淚縱橫,在一旁的李綱也為之動容。
一天,李綱在朝見時與宗澤偶遇,有過一番談話,他們談及國事,為之心痛不已,也為抗金大業慷慨激昂。當時,開封府缺一名獨當一面的大臣駐守,李綱就向高宗極力推薦宗澤:「綏復舊都,非宗澤不可。」
趙構早想著重用宗澤,李綱也欲留他共同主持大局,但是以黃潛善、汪伯彥為首的主和派大臣屢屢從中作梗。最後,高宗只是授宗澤以龍圖閣學士、知襄陽府,讓他去建設大後方。
李綱立馬察覺此事不對勁,便一再奏請擢宗澤為開封府尹、東京留守,大力支持其對京城的防禦。
這些「糟老頭子」犟得很,趙構自知拗不過,只好同意。
孤獨的宗澤,在主和派輕蔑的眼光中,來到那座已經沒有皇帝的都城。
開封不久前慘遭金兵劫掠,盜賊蜂起,人心惶惶,城中殘破不堪,「凍餒死者十五、六」,早已看不出一絲《清明上河圖》中那盛世繁榮的氣象。
同樣孤立的李綱,在朝中不斷受到黃、汪等黨羽的攻擊。
有人說李綱,「名浮於實,而有震主之威,不可以相。」還有人老調重彈,用之前北宋大臣的言論抨擊他:「為金人所惡,不宜為相。」
李綱與宗澤有共同主張,他們一人在朝,一人在汴,艱難支撐起抗金的大旗。
他們都善於利用河北、河東等地民兵。
當時,各地義兵興起,打著勤王的旗號,卻各懷心思,難以統一調度。但朝廷眼中的這些「匪」「寇」兵力雄厚,是李綱與宗澤一心爭取的對象。
淮南的杜用,山東的李昱,襄陽的李孝忠,都被李綱調兵遣將一一討平,降者多達十餘萬,歸於諸將帳下,聽候調遣,構成一道橫跨數州的防線,只待渡河討伐金兵。
京西、淮南、兩河一帶的「草頭王」們也在宗澤愛國精神的感召下,紛紛加入匡扶宋室的隊伍。
濮州義軍的首領王善,自稱手下有數十萬之眾,兵車萬乘,本來不給宗澤好臉色看,還想出兵占領汴京。
宗澤聽聞此事,親自前去勸降,單騎入營與王善相見,請他加入抗金大軍,說:「朝廷正當危難之時,如果有一兩位如你這樣的人,豈還會有敵患?今日就是立功的好時機,機不可失啊。」
王善一看,宗澤年近七旬,還一心為國為民,極富誠意,對他佩服不已,二話不說,解甲歸降。
壽春人丁進,江湖人稱「丁一箭」,聚眾數萬人,聽聞宗澤的威名,帶兵前往京城近郊求見。
宗澤的部下都擔心有詐,宗澤卻說:「精誠所至,金石為開,何況是人呢?」
丁進到後,宗澤親自接見,像對待老部下一樣與他親切交談。丁進十分感動,當即請宗澤前去視察他的部隊。宗澤毫不懷疑,第二天就去慰問了丁進的軍隊。
從此,丁進所部歸入宗澤麾下,成為保衛汴京的一支生力軍。如果發現隊伍中有人懷有二心,丁進會果斷地將其斬殺。
除此之外,還有外號「沒角牛」的楊進、李貴、王大郎、王再興等各自擁兵割據一方,宗澤曉以大義,將他們一一招降。
李、宗二人對主戰派的同志,也都是知人善任。
李綱舉薦了張所、傅亮等主戰派,此二人分別被任命為河北路招撫使與河東路招撫使。
張所在北宋當過御史,宋朝向金朝割地求和時,他主張招募河北民兵救援京城,後來黃潛善被高宗重用後,他又上疏直言黃潛善姦邪誤國,因此被貶到江州。這些主戰派一個個都脾氣火爆。
得到李綱提拔後,張所來到河北招攬豪傑,整頓軍備。一個因越職言事而被逐出軍營的青年,在此時來到河北投奔張所,後來歸於宗澤帳下。
他,就是岳飛。
岳飛只是一個低級軍官,敢於說真話,此前上書論事,惹禍上身。
他竟然譴責「黃潛善、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,奉車駕日益南,恐不足系中原之望」,還義正辭嚴地請高宗「親率六軍北渡,則將士作氣,中原可復」。
這樣一個刺兒頭,深得宗澤器重。
有一次,岳飛觸犯了軍法,本來要嚴加處置。宗澤一見到他,交談之後,發現他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將才。
正值金人入侵汜水,宗澤給了岳飛將功補過的機會,讓他帶五百名騎兵作為先鋒部隊出戰。
岳飛初出茅廬,就盡顯軍事奇才,在這次遭遇戰中痛擊金軍。岳飛凱旋後,宗澤赦免了他的罪,並升他為統制,年輕的岳飛由此成名。
 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