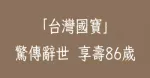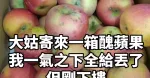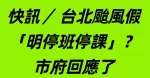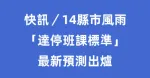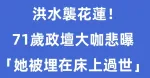4/4
下一頁
大宋居然糟蹋了這麼牛X的人物

4/4
▲宋高宗,1127-1162年在位。圖源:網絡
建炎二年(1128年)春,留守東京的宗澤已經招撫各地義軍百萬之眾,且積蓄了半年軍糧,他多次上書痛斥黃、汪一黨懦弱無能,請皇帝還京掌國,卻一次次石沉大海。
宗澤知道趙構「恐金症」晚期,可能不相信他的話,還在奏疏中誠懇地說:「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,臣有一子五孫,甘被誅戮。」
在一次與金兵的交戰中,宗澤擒獲了遼國舊將王策,親自為其鬆綁,請他坐於堂上。
兩人都與金人有國讎,宗澤對他說:「契丹本來是我大宋兄弟之國,如今女真辱我主,又將你們滅國,我們應當同心協力,一雪前恥啊!」
王策聽宗澤這麼說,感動得稀里嘩啦,也不計較北宋之前背信棄義,就將金人的虛實全部告知宗澤,進一步堅定了宗澤抗金的決心。
宗澤打聽到兩河州縣金軍兵力空虛,前後上疏二十多次,懇請趙構「早還華闕」,發兵北伐。宗澤的文書如雪片般飛來,可趙構都不為所動。
一直拖到當年七月,宋高宗仍然沒有表態,宗澤的部隊遲遲無法進軍。
宗澤望眼欲穿,期盼著皇帝移駕開封,希望卻如此渺茫。
他病倒了。
年邁的宗澤憂憤成疾,背上生疽,從此一病不起。
當將領們在榻前問候時,他支撐著坐起來,說:「我本來沒病,只因二帝蒙塵,心生憂憤。希望諸位能夠奮力殲敵,那樣我就死而無憾了。」
眾將聽罷,淚流不止,表示一定不會辜負宗澤的囑託。
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里,宗澤反覆悲吟杜甫寫諸葛亮的詩句「出師未捷身先死,長使英雄淚滿襟」,沒有一句話談及家事。
臨終前,他大呼三聲「渡河」,悲憤去世。
宗澤的兒子宗穎,將其遺表上呈高宗,表中最後幾句寫道:「屬臣之子,記臣之言,力請鑾輿,亟還京闕,大震雷霆之怒,出民水火之中。夙荷君恩,敢忘尸諫!」
不知宋高宗讀罷,心中是何感受。
宗澤的理想,隨他消逝在東京夢華之中。李綱卻在失意的煩惱之中,又艱難地活了13年。每次宋金議和,這個老憤青都要上書把主和派痛罵一頓。
紹興八年(1138年),主和派的秦檜入朝執政,南宋再一次與金朝議和。
早已遠離中樞的李綱雖然失去存在感,但還是投了反對票,上書高宗,言辭激烈,其中說到,金人毀我宗廟,迫害二帝,他們是我們的仇敵,我們是他們的心腹大患,豈有講和的道理?
李綱直接懟宋高宗,責問他:「何況現在還有半壁天下,臣民都擁戴大宋,如果陛下與有識之士一起謀劃,還能有所作為。怎可忘記祖宗的基業和百姓的期望,不加考慮就急於向金人屈服,希望苟延性命於旦夕之間呢?」
天底下也沒幾個人敢這麼跟皇帝說話了。
當時主和的大臣認為李綱忤逆,請求將其治罪。高宗卻為李綱開脫,說:「大臣當如此矣。」
次年,趙構想再次起用李綱,任命他為荊湖南路安撫大使。抱病的李綱對朝廷早已失望,極力推辭。
他告訴皇帝,老臣迂腐,不善於明哲保身,總是上書煩擾陛下,這幾年,臣頻繁反覆地受提拔、貶斥,不僅有損於陛下知人善任的英明,也有損於國體。
這番話,好像還有幾分諷刺的意思。昨天的你對我愛答不理,今天的我讓你高攀不起。
高宗看罷,也不願強求。
又過了一年,58歲的李綱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。
李綱一生六起六落,自罷相後漂泊四方,壯志難酬。晚年的他屢遭貶謫,身體日衰,以「病牛」自喻,曾在謫居鄂州期間,寫了一首《病牛》詩:
耕犁千畝實千箱,力盡筋疲誰復傷?
但得眾生皆得飽,不辭羸病臥殘陽。
任何一個時代,都不缺李綱、宗澤這樣的硬骨頭。可又有多少時代,容得下這樣的硬骨頭?
建炎二年(1128年)春,留守東京的宗澤已經招撫各地義軍百萬之眾,且積蓄了半年軍糧,他多次上書痛斥黃、汪一黨懦弱無能,請皇帝還京掌國,卻一次次石沉大海。
宗澤知道趙構「恐金症」晚期,可能不相信他的話,還在奏疏中誠懇地說:「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,臣有一子五孫,甘被誅戮。」
在一次與金兵的交戰中,宗澤擒獲了遼國舊將王策,親自為其鬆綁,請他坐於堂上。
兩人都與金人有國讎,宗澤對他說:「契丹本來是我大宋兄弟之國,如今女真辱我主,又將你們滅國,我們應當同心協力,一雪前恥啊!」
王策聽宗澤這麼說,感動得稀里嘩啦,也不計較北宋之前背信棄義,就將金人的虛實全部告知宗澤,進一步堅定了宗澤抗金的決心。
宗澤打聽到兩河州縣金軍兵力空虛,前後上疏二十多次,懇請趙構「早還華闕」,發兵北伐。宗澤的文書如雪片般飛來,可趙構都不為所動。
一直拖到當年七月,宋高宗仍然沒有表態,宗澤的部隊遲遲無法進軍。
宗澤望眼欲穿,期盼著皇帝移駕開封,希望卻如此渺茫。
他病倒了。
年邁的宗澤憂憤成疾,背上生疽,從此一病不起。
當將領們在榻前問候時,他支撐著坐起來,說:「我本來沒病,只因二帝蒙塵,心生憂憤。希望諸位能夠奮力殲敵,那樣我就死而無憾了。」
眾將聽罷,淚流不止,表示一定不會辜負宗澤的囑託。
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里,宗澤反覆悲吟杜甫寫諸葛亮的詩句「出師未捷身先死,長使英雄淚滿襟」,沒有一句話談及家事。
臨終前,他大呼三聲「渡河」,悲憤去世。
宗澤的兒子宗穎,將其遺表上呈高宗,表中最後幾句寫道:「屬臣之子,記臣之言,力請鑾輿,亟還京闕,大震雷霆之怒,出民水火之中。夙荷君恩,敢忘尸諫!」
不知宋高宗讀罷,心中是何感受。
宗澤的理想,隨他消逝在東京夢華之中。李綱卻在失意的煩惱之中,又艱難地活了13年。每次宋金議和,這個老憤青都要上書把主和派痛罵一頓。
紹興八年(1138年),主和派的秦檜入朝執政,南宋再一次與金朝議和。
早已遠離中樞的李綱雖然失去存在感,但還是投了反對票,上書高宗,言辭激烈,其中說到,金人毀我宗廟,迫害二帝,他們是我們的仇敵,我們是他們的心腹大患,豈有講和的道理?
李綱直接懟宋高宗,責問他:「何況現在還有半壁天下,臣民都擁戴大宋,如果陛下與有識之士一起謀劃,還能有所作為。怎可忘記祖宗的基業和百姓的期望,不加考慮就急於向金人屈服,希望苟延性命於旦夕之間呢?」
天底下也沒幾個人敢這麼跟皇帝說話了。
當時主和的大臣認為李綱忤逆,請求將其治罪。高宗卻為李綱開脫,說:「大臣當如此矣。」
次年,趙構想再次起用李綱,任命他為荊湖南路安撫大使。抱病的李綱對朝廷早已失望,極力推辭。
他告訴皇帝,老臣迂腐,不善於明哲保身,總是上書煩擾陛下,這幾年,臣頻繁反覆地受提拔、貶斥,不僅有損於陛下知人善任的英明,也有損於國體。
這番話,好像還有幾分諷刺的意思。昨天的你對我愛答不理,今天的我讓你高攀不起。
高宗看罷,也不願強求。
又過了一年,58歲的李綱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。
李綱一生六起六落,自罷相後漂泊四方,壯志難酬。晚年的他屢遭貶謫,身體日衰,以「病牛」自喻,曾在謫居鄂州期間,寫了一首《病牛》詩:
耕犁千畝實千箱,力盡筋疲誰復傷?
但得眾生皆得飽,不辭羸病臥殘陽。
任何一個時代,都不缺李綱、宗澤這樣的硬骨頭。可又有多少時代,容得下這樣的硬骨頭?
 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