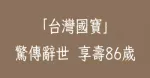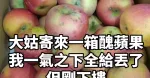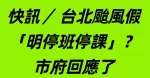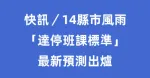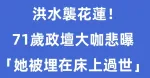1/3
下一頁
生前罵名遍天下,死後卻成民族之光,他的名字如今已鮮為人知

1/3
生前罵名遍天下,死後卻成民族之光,他的名字如今已鮮為人知
馬相伯,今天我們提起他,很多人一臉茫然。
然而這個人曾經可是名揚天下,只不過是惡名。
他被罵成「漢奸」「國賊」,臭名遍天下。
可如果你真的把他就此比作秦檜、汪精衛、德王之流,那你就把他想簡單了。
人家可是復旦大學的創始人;蔡元培、于右任、李叔同、陳寅恪這些如雷貫耳的大師,要麼是他的學生,要麼受過他的提攜和影響,尊他為師長;他92歲高齡投身抗日,演講、賣字籌款,用百歲生命為國家吶喊……
你可能會更加困惑:
這樣一個「民族之光」級別的人物,怎麼會和「漢奸」這種詞扯上關係?
被時代誤解的「賣國賊」
馬相伯的「漢奸」罵名,主要源於兩件事,而這兩件事,都和他進入李鴻章幕府,投身洋務運動的生涯有關。
第一件,是那筆「消失」的巨額貸款。
大約在1886年,清廷搞洋務,要建海軍,缺錢。
李鴻章派馬相伯這個精通外語和西方事務的人才去美國籌款。
馬相伯不負眾望,憑著過人的才智和口才,竟然說服了24家美國銀行,談成了一筆高達5億元的巨額貸款。
這是什麼概念?這筆錢在當時足以打造一支亞洲頂級的艦隊。
然而,消息傳回國內,朝堂之上炸了鍋。
御史們紛紛上書彈劾,罪名是李鴻章「勾結洋人,出賣國家」,說這筆貸款是引狼入室的陰謀。
在那個普遍排外、視一切「洋務」為洪水猛獸的年代,這種指控極具殺傷力。
最終,清廷迫於壓力,否決了這筆貸款。
馬相伯辛苦奔走換來的成果化為泡影,自己還被報紙痛罵為「漢奸」,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。
他想用外國的錢為中國辦事,卻被自己人當成了敵人。
如果說這件事還只是事業上的打擊,那麼第二件事,則直接刺穿了他的靈魂。
1895年,甲午戰敗,李鴻章作為代表赴日本馬關談判。
馬相伯因為精通多國語言,作為翻譯隨行。
我們都知道,《馬關條約》是一個何等屈辱的條約。
當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,全國上下一片沸騰,所有的怒火都傾瀉在談判代表身上。
李鴻章首當其衝,而作為他身邊最顯眼的「洋務幹將」,馬相伯和他的哥哥馬建忠,也一同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,被斥為「賣國賊」、「漢奸」。
民眾的憤怒可以理解,但在那個信息閉塞的年代,沒人會去深究一個翻譯在談判桌上究竟能起多大作用。
他們只看到馬相伯出現在那個喪權辱國的場合,這就足夠了。
這種來自整個社會的口誅筆伐,已經讓馬相伯痛不欲生。
更致命的打擊來自家庭。
他的母親,一位虔誠的教徒,本就因他脫離教會而心存芥蒂,如今又聽說兒子參與了「賣國條約」,在巨大的羞憤和悲痛中,臨終前拒絕見他最後一面。
至親的隔閡,比千夫所指更傷人。
這成了馬相伯一生都無法癒合的創傷。
他想救國,卻被國民唾罵;他想盡孝,卻被母親拒絕。
這種深不見底的孤獨和痛苦,徹底擊垮了他對政治的熱情。
他意識到,在一個沉睡的、封閉的國度里,想要通過官場和外交來實現「自強」的理想,無異於痴人說夢。
傾盡所有,只為點燃一支火炬
心灰意冷的馬相伯,在60歲那年做出了一個震驚所有人的決定。
他將自己名下所有的家產——位於松江、青浦等地的3000畝良田和所有房產地契,全部捐出,要創辦一所「中西大學堂」。
他的邏輯很簡單:政治救國之路走不通,那就從根上做起,教育救國。
他有一句名言:「自強之道,以作育人才為本,求才之道,尤以設立學堂為先。」
1903年,馬相伯租用徐家匯天文台的舊址,創辦了震旦學院。
他親自擔任院長,並立下了「崇尚科學、注重文藝、不談教理」的校訓。
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的。
馬相伯,今天我們提起他,很多人一臉茫然。
然而這個人曾經可是名揚天下,只不過是惡名。
他被罵成「漢奸」「國賊」,臭名遍天下。
可如果你真的把他就此比作秦檜、汪精衛、德王之流,那你就把他想簡單了。
人家可是復旦大學的創始人;蔡元培、于右任、李叔同、陳寅恪這些如雷貫耳的大師,要麼是他的學生,要麼受過他的提攜和影響,尊他為師長;他92歲高齡投身抗日,演講、賣字籌款,用百歲生命為國家吶喊……
你可能會更加困惑:
這樣一個「民族之光」級別的人物,怎麼會和「漢奸」這種詞扯上關係?
被時代誤解的「賣國賊」
馬相伯的「漢奸」罵名,主要源於兩件事,而這兩件事,都和他進入李鴻章幕府,投身洋務運動的生涯有關。
第一件,是那筆「消失」的巨額貸款。
大約在1886年,清廷搞洋務,要建海軍,缺錢。
李鴻章派馬相伯這個精通外語和西方事務的人才去美國籌款。
馬相伯不負眾望,憑著過人的才智和口才,竟然說服了24家美國銀行,談成了一筆高達5億元的巨額貸款。
這是什麼概念?這筆錢在當時足以打造一支亞洲頂級的艦隊。
然而,消息傳回國內,朝堂之上炸了鍋。
御史們紛紛上書彈劾,罪名是李鴻章「勾結洋人,出賣國家」,說這筆貸款是引狼入室的陰謀。
在那個普遍排外、視一切「洋務」為洪水猛獸的年代,這種指控極具殺傷力。
最終,清廷迫於壓力,否決了這筆貸款。
馬相伯辛苦奔走換來的成果化為泡影,自己還被報紙痛罵為「漢奸」,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。
他想用外國的錢為中國辦事,卻被自己人當成了敵人。
如果說這件事還只是事業上的打擊,那麼第二件事,則直接刺穿了他的靈魂。
1895年,甲午戰敗,李鴻章作為代表赴日本馬關談判。
馬相伯因為精通多國語言,作為翻譯隨行。
我們都知道,《馬關條約》是一個何等屈辱的條約。
當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,全國上下一片沸騰,所有的怒火都傾瀉在談判代表身上。
李鴻章首當其衝,而作為他身邊最顯眼的「洋務幹將」,馬相伯和他的哥哥馬建忠,也一同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,被斥為「賣國賊」、「漢奸」。
民眾的憤怒可以理解,但在那個信息閉塞的年代,沒人會去深究一個翻譯在談判桌上究竟能起多大作用。
他們只看到馬相伯出現在那個喪權辱國的場合,這就足夠了。
這種來自整個社會的口誅筆伐,已經讓馬相伯痛不欲生。
更致命的打擊來自家庭。
他的母親,一位虔誠的教徒,本就因他脫離教會而心存芥蒂,如今又聽說兒子參與了「賣國條約」,在巨大的羞憤和悲痛中,臨終前拒絕見他最後一面。
至親的隔閡,比千夫所指更傷人。
這成了馬相伯一生都無法癒合的創傷。
他想救國,卻被國民唾罵;他想盡孝,卻被母親拒絕。
這種深不見底的孤獨和痛苦,徹底擊垮了他對政治的熱情。
他意識到,在一個沉睡的、封閉的國度里,想要通過官場和外交來實現「自強」的理想,無異於痴人說夢。
傾盡所有,只為點燃一支火炬
心灰意冷的馬相伯,在60歲那年做出了一個震驚所有人的決定。
他將自己名下所有的家產——位於松江、青浦等地的3000畝良田和所有房產地契,全部捐出,要創辦一所「中西大學堂」。
他的邏輯很簡單:政治救國之路走不通,那就從根上做起,教育救國。
他有一句名言:「自強之道,以作育人才為本,求才之道,尤以設立學堂為先。」
1903年,馬相伯租用徐家匯天文台的舊址,創辦了震旦學院。
他親自擔任院長,並立下了「崇尚科學、注重文藝、不談教理」的校訓。
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的。
 呂純弘 • 12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2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9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